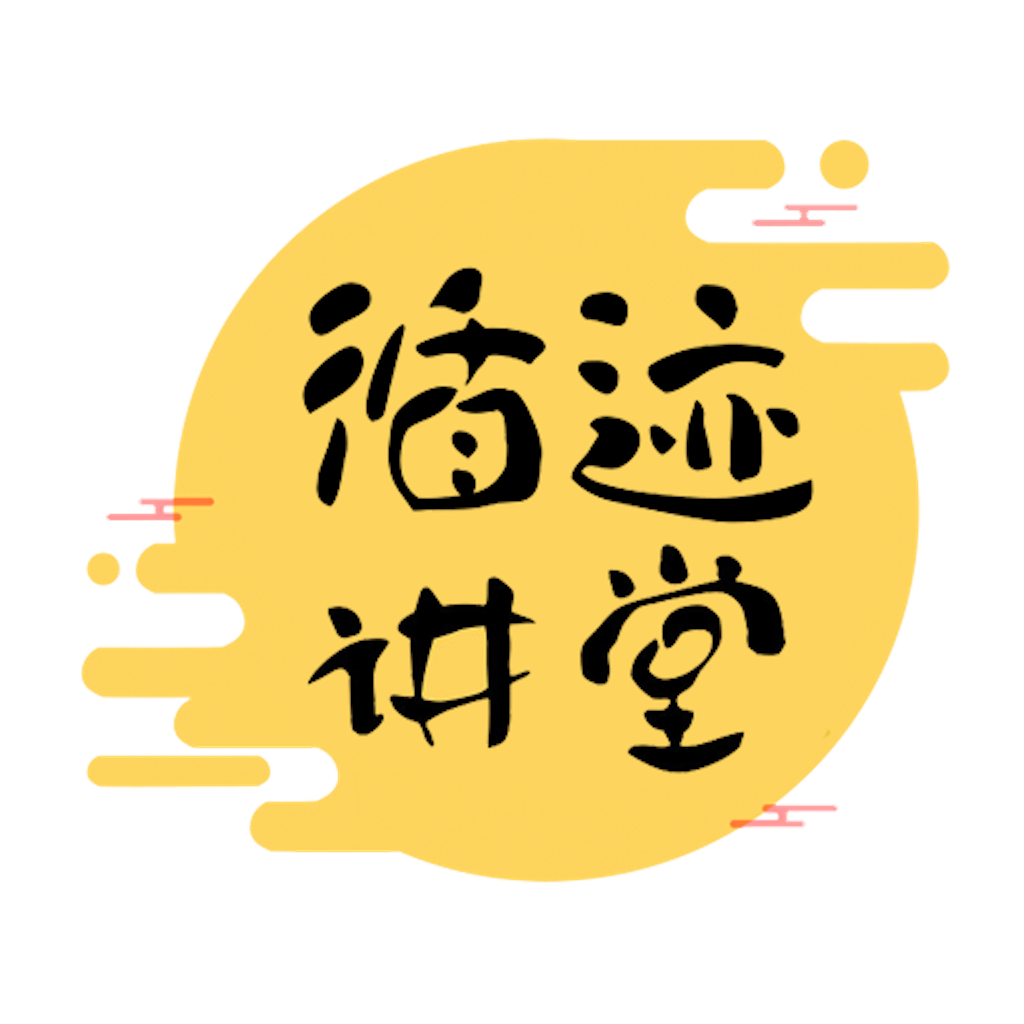五四运动是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件。
狭义的五四运动仅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汇聚在街头抗议巴黎和约。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1919年前后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

青年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标语
最早的启蒙以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体现,通过大量文学作品的表达反传统的思想。思想启蒙在学生群体表现最为显著,这也是爆发学生爱国运动的一大原因。
而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回响,引发救亡情绪和民族主义倾向让启蒙运动变质和转向,最终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程。

五四运动
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人们开始寻求更快速改造中国的方法,受俄国影响的知识分子更迫切寻求一剂猛药,认为启蒙运动成效太慢,纷纷放弃了启蒙。
当时知识分子对启蒙的放弃,不仅深切影响了当时的青年,更影响之后的一代又一代青年。
曾经高举的“德先生”、“赛先生”大旗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明显分歧的不同政治思想在中国上空冲突、激荡。
对于五四的印象也渐渐符号化、脸谱化,以至于人人都说“纪念五四运动”、“继承五四精神”,可是到底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却十分模糊,被掌握话语能力的人任意定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日人投毒
1919到1920年,五四运动的风潮不仅在学生中席卷,其影响也在推向下层民众。
上海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中心之一,除了学生运动之外,上海有关机构也动员市民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民间的暗潮被上海租界当局察觉,感觉到民众的反日情绪正在升高。

《新申报》发行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号外
1919年5月18日,上海街头出现学生和游民从人们头上抢走日本产的草帽并予以损毁,黄包车夫拒绝搭载日本人,娱乐场所也高喊“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
不知从何日起,上海民众开始出现“日本人在上海饮水中投毒”的谣言。
传言必须有炮制者和传播者两种力量同时推动才能真正影响民众,日人投毒的谣言,其炮制者为谁,出于何种目的已经不得而知。
但传播者当中有不少是先前鼓动上海市民反日的力量。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未必知道“我们”与日本人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与“我”有什么干系,谣言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我们”到“我”之间的空白,把空洞的“爱国仇日”和具体的个人生存强行联系起来,这就是鼓动市民反日的人加入谣言传播的理由之一。

百年前的老上海
当时上海的新闻界总体是倾向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大量新闻记者甚至都是刚刚参加完五四学生运动,就毕业加入报馆,反帝爱国情绪十分强烈。
于是,上海的各大报纸,经常报道与日人投毒有关的报道。
但总体而言,当时的上海报纸基本还是遵守了新闻真实原则,对此类传言会在标题中明确注明“传”、“谣传”等字样。
不过以当时的民众平均智识水平而言,即使新闻标题明确写出此事件是传言,也不会有多少人分辨谣言和真实,只要报纸登载了就是真的,人就会相信。
这就是舆论“引导”的力量。

“五四运动”中军警和学生辩论
谣言愈演愈烈,青年学生开始劝导市民自行囤积饮用水,以防日本人在自来水中投毒。
此举波及上海自来水公司的营业,用户纷纷打电话询问是否有抓获自来水投毒者,自来水公司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否认投毒之说。
日人投毒的谣言与社会的反日情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上海的“三罢”斗争遂得以如火如荼的进行。
据上海媒体报道,反日情绪引发的中外冲突屡见不鲜,日本人在上海坐车、购物、行走,均可能引发与上海市民的口角乃至斗殴。
民众排日,主要原因并非“爱国”,主要是恐惧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这种排外情绪不仅体现在对日本人身上,所有生活环境中的陌生人都可能被看作危险因素而予以排斥。

1917年,上海董家渡自来水厂的沙沥池和唧机站
其中,由于口音和相貌与本地人有区别,很多外地中国人也受到民众的攻击,甚至那些曾经煽动民众排日的青年学生,此时也成为被市民排斥的对象。
养蛊者被反噬,也是哭笑不得。
五四运动刚发生不久,上海市民就以排日的行为开展“纪念”。
民众排日,根本与爱国无关,广泛流传的日人投毒谣言主要体现出民众对自身安危的极度焦虑。
打倒军阀
1923年,距离五四运动过去四年了。
这几年中,中国的政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当时的全国学生总会正式发电要求每年5月4日举行纪念大会,五四纪念活动变成反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势力大集结的平台。
1924年,国共两党重要人物汪精卫、叶楚怆、胡汉民、瞿秋白等或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从理论高度阐述“五四”的伟大意义,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开启了“诠释”五四运动的理论竞赛。
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主旨在外交,“争取国权,驱除列强”是核心。

学生的街头演讲
随后引发的民族主义风潮,乃至抵制外国货,打骂外国人等民粹主义举动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五四运动本身的目的主要是对外。
对内方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希望那些“卖国”的政客下台,以“火烧赵家楼”为主要表现。
但随后的几年,“外争国权”声音渐微,“内除国贼”逐渐走强,其内涵也被诠释为推翻北洋政府当局的统治。
在当时的南方革命当局提倡下,五四纪念活动从自发的、分散的民间运动,转而变成官方的、有序的政治活动。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
汪精卫在上海率先提出要将五四纪念活动办为“长期有组织有规律的活动”,其纪念的对象也从当初的“德先生”、“赛先生”变成“孙先生”——孙中山遗像、孙总理遗嘱、广州国民政府旗帜。
有趣的是,北洋军阀当局并未阻挠青年们开展旨在推翻他们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五四纪念活动能够成为一项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分裂为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和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两大势力。总体上以南京国民政府势力较大,绝大多数军事将领听命于蒋介石。
当年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又成了南京方面攻击武汉方面的重要舞台,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纷纷借大会的机会登台演讲,批判武汉国民政府。
蒋介石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五四运动为人民谋平等自由,“必须拥护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接受指导,完成国民革命”。
蒋介石的宣言,彻底实现了由掌握话语能力的人诠释五四运动,而1919年5月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应该纪念什么,渐渐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1929年恰逢五四运动十周年,国民党天津市当局发表了《为五四运动告全市青年》的通告,当中说:“本党现负领导民众,领导青年之责,当然责无旁贷,而一般民众一般青年要确信国民革命是中国民族唯一的出路,而领导国民革命的,唯一的是中国国民党。”

1930年,中原大战三位主角,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再一次充分运用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为国民党派系斗争造势。
南京方面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反蒋联盟力量比喻成“一切破坏国家利益之反动势力”,号召全国人民拥护蒋介石,反对反蒋联盟。
当初高谈“五四”是为了打倒军阀,此时高谈“五四”,却是为了标榜军阀混战的合法性,实在让人唏嘘。
当时的青年对这些宣传究竟有何反响,今天已经很难彻底弄清楚。
但1929年的青年,绝大多数都还经历过1919年的5月4日,他们是否知道,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其意义在变成“打倒军阀”的那一刻起,就再也回不去初心了。
抗日动员
1928年,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济南,日军借口革命军抢劫济南城内的日本侨民,突然发兵杀害中国军人、民众六千余人,并占领济南。史称“济南惨案”。
凑巧的是,日军发难的第二天就是五四运动纪念日,各地借五四纪念动员民众抵制日本的侵略行径。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很多人不满东北不抵抗,对国民党当局不满。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
在五四纪念活动当中,官方通稿不遗余力地强调“抗日救国并非贴标语喊口号就能成功”。
但国民党当局对国内舆论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尽管官方大力鼓吹激进口号有害论,却完全无法禁止民众高涨的抗战热情。
此时,虽然五四纪念活动已经是官方活动,主要议程都由官方主导,但绝大多数民众尚未忘记1919年的学生运动,青年学生也没有忘记当初“火烧赵家楼”的热情,出现了借五四纪念活动再掀学生运动的苗头。
眼看情势不对,国民党当局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禁止举行各种五四纪念会,北京大学甚至取消了照例5月4日的一天休假。
当局的做法极大地伤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心,更催生出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思想上倾向于不同于国民党当局的其他政治派别,这恐怕是极尽限制、打压之能事的国民党始料未及的。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迎来了五四运动二十周年。

1938年8月,山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青年队在晋西演出时留影 苏静摄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
与此同时,一篇名为《五四运动》的文章,把五四运动定性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国民党也不甘落后,同样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
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中国青年的首要任务是战胜日本法西斯。但是几年之后,国民党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
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重定3月29日为青年节,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五四退化为仅在文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运动,而非政治运动。这一转变企图打压乃至磨灭青年的五四记忆,控制青年思想。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强烈反对篡改青年节日期的行为,1944年西南联大举办了“捍卫五四精神,发扬五四传统”座谈会,吴晗在会上表示,“五四的任务远没有结束”。

青年吴晗
吴晗口中“五四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作为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应该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初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北洋当局统治早已结束,但当时的青年所反对的并非北洋当局本身,中国的问题也绝不是改朝换代就能解决的。
即使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些对中国“下猛药”的方案,但“下猛药”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启蒙,也不意味着启蒙已经成功或者失败。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所有人都在思考国家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吴晗适时提出“五四的任务”,打破掌握话语能力人的诠释垄断,让国家重回进步轨道,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渐失话语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五四本身的记忆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被各种强力话语能力重新诠释的“五四”。
1959年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邓颖超同志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给青年们的信》。信中说:
“四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军阀连年混战的祸害,封建买办的反动政府卖国求荣,压迫和奴役人民。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青年,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经常受着失业、失学、贫穷饥饿、疾病死亡的侵袭。妇女的处境特别悲惨,她们不仅在各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甚至常常被当作商品买卖。当时的这一切情况,是你们这一代青年难以想象的。”
“严重的民族危机,无法忍受的苦难生活,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更鼓舞了这一斗争。1919年,美、英、法、日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胜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赃,在巴黎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不仅否决了中国人民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正当要求,而且公然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一贯丧权辱国的北京军阀政府竟准备妥协签字。这引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怒,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起来。”
邓颖超同志在信中首先描述了五四运动当时的社会状况,把五四运动完全表述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诠释体系中,五四之前的启蒙完全消失了,五四期间的文化、文学、思想方面的变革也都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彻底失踪了。
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官方占据了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的绝大多数空间。
普通青年即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更没有热情真正投入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和五四精神的思考,转而变成完成某种规定动作。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在海峡的另一边,1960年,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之邀,用与记者对谈的方式,发表了颇长的一篇谈话《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
胡适在谈话中表示:
“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所以从此之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就变质了,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
可以看出,胡适对于从启蒙到政治,感到十分遗憾。
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开始是支持、鼓励,到晚年就有所保留,认为群众的冲动、不理性,湮灭了运动原本所想要达到的追求,再加上背后有人推波助澜,最终将运动推向激烈的方向去了。
2018年,余英时先生在回忆和访谈中,多次提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他继承了胡适的思想,认为这是一场文化运动,而其核心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在五四运动后续的演变中,德、赛先生二先生逐渐退居幕后
只不过这笔遗产似乎在新的时代缺失了存在感,有待今人好好发掘。
失去话语的不止两位先生,也包括广大青年。
不知何时起,我们总是能够在新闻里读到“热烈反响”、“广泛讨论”,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听过哪个青年到底“讨论”了什么,有什么“反响”。
当两位老祖宗早已连牌位都不见,也就勿怪只有人修祠堂,没有人拜祠堂了。
结语
如何纪念五四运动,是一部有趣的历史。
百年来,人们从发动、经历,到诠释、反思,最后失语、疏离,体现了百年来这个国家的思想史是如何在外力的作用下演进发展的。
有人说,五四运动之后,已经完成了启蒙的历史重任。既然已经完成,那两位先生的名字也就无需再提了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