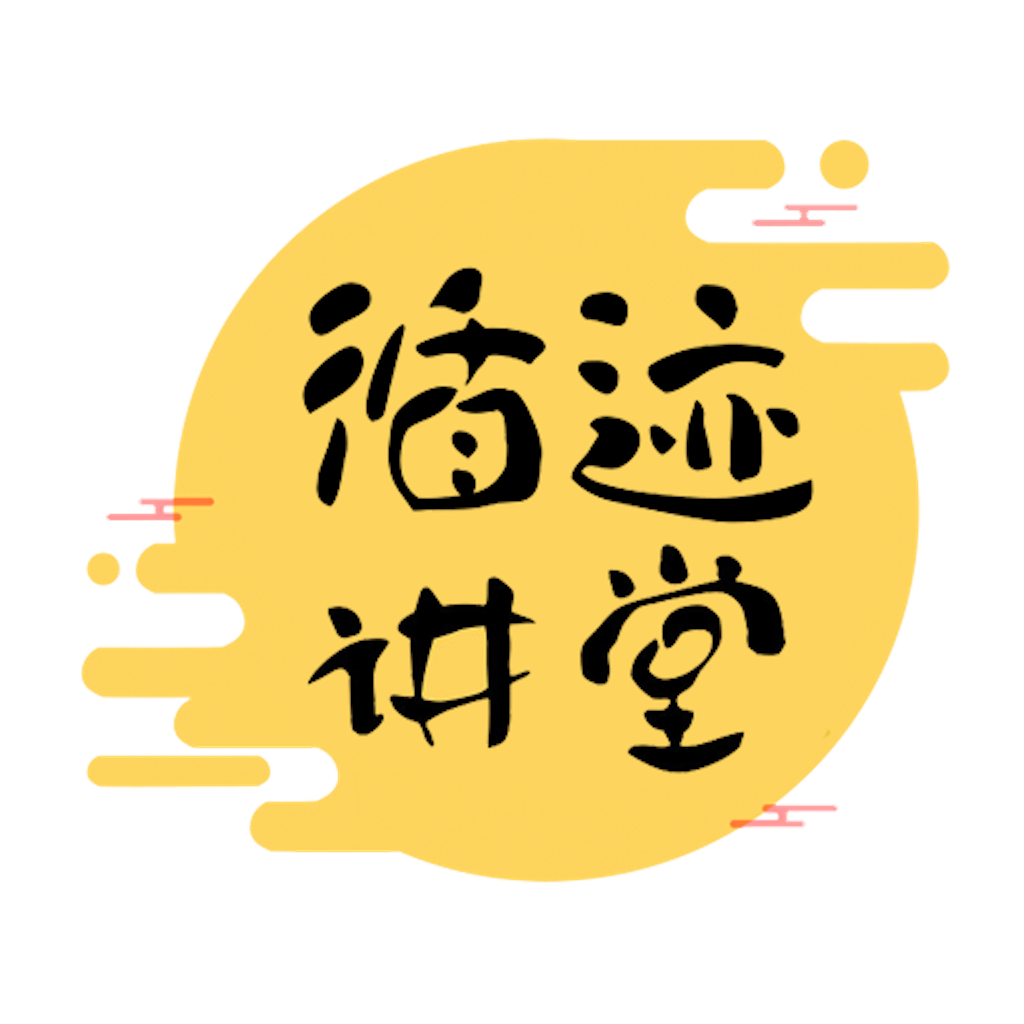2019年夏天,我在澳洲旅游。
在一个有众多外国留学生的城市里,我目睹了一场来自另一个国家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分为两大阵营开展的对垒,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留学生。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那群来自比较大地区阵营中的青年,并不喜欢与对方辩理,更喜欢以高声爆粗口来形成“气势”压倒对方。他们还喜欢声称代表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声音。
在这群青年中,有一个女孩,是我出国之前在酒吧认识的。
那是几年前的万圣节前夜,这间酒吧正在举办一支摇滚乐队的演唱会。95后、00后的青年,可能不知道摇滚在80、90年代意味着什么,被赋予哪些意义,只觉着热闹、帅气,这个女孩也一样。
否则她就不会出去留学了还要参加这种旨在用音量压制对手的聚会。

澳洲乐队AC/DC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没有发表任何与女孩不同的意见,不想让她发现她其实根本代表不了我,因为我在这座城市的旅途还需要她来增光添色。
不失时机地沉默,也许就是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身上特有的狡黠和鸡贼吧。
在女孩的朋友圈里,没有任何与那次对垒有关议题的讨论,但这并不代表她的生活不丰富。
她学习英语、学习烘焙手艺、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去南半球许多角落旅行,20出头就能够不惑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及凭借相同的留学经历结交值得干杯的朋友,岁月静好。
“后浪”招惹谁了
5月4日某站推出了那段引发广泛讨论的视频后,我发现我所认识的这位95后女孩,不就是视频中所说的“后浪”群体吗?
自那段视频发布后,某站的一部分拥趸争相转发,并对视频里对自己的“准确”吹捧沾沾自喜。但同时网络上也争相涌现对这段视频演说的嘲讽和反对。

B站的后浪视频
那些嘲讽的声音本身,确实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如此巨大的声浪要说背后没有一点推动力也是绝不可能的。
除了很多一贯独立思考的声音之外,也不乏商业号跟进,在其他社交平台如某乎等也呈现“翻车”的状况。看起来,某站得罪的人着实不少。
于是就有人认为,那些嘲讽和反对仅仅是因为“嫉妒”、“酸”。

翻车就是因为“嫉妒、酸”
人们为什么会“酸”这段视频演讲的制作者“不是我”,而是某站呢?
我们常说,当一个人看我不爽,可能是他的问题,当所有人都看我不爽的时候,大概率是我自己的原因。那我们就来看看某站自身有什么问题。
最近在文化界,出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曾经一统天下的官办文化产品输出机构如电视台、报社等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资本大鳄。
这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他们与具备权力背景的机构深度合作,是权力的传声筒,通过资本与权力合一的方式取得网络文化传播的垄断地位。
对于其他资本来说,即使他们站在与某站相同的立场上,甚至更加使劲的在同一立场鼓噪,也没法撼动垄断的权资联盟,没法取某站而代之。
既然如此,何不与那些向来不被“主流”待见的独立声音共进退,干脆反其道而行之,走民意路线。
天下苦垄断久矣,在大力提倡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今天,文化市场的营商环境,就不是营商环境了么?
“后浪”真的是那个后浪吗?
在小说1984里,大洋国的高层编纂了一本《新话词典》。
所谓“新话”,就是创造新词、废除了不合适的词、消除词原有的多种含义以及重新诠释旧词。在“新话”中,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允许存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这让我想起了澳洲那场对垒,一少数人妄言他们能代表绝大多数人,不正是“新话”在社会中的表现吗?
虽然现实中不存在小说描绘的情形,但我们谁都不会傻到去感叹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时代遇到了“最好的我们”。

乔治·奥威尔
处于当今这个时代的我们,虽然没有《新话词典》,但似乎确实有一种新话式的趋势,这种趋势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给社会,尤其是看起来不经意的网络娱乐的形式。
在“后浪”演讲中,我们看到:撰稿人用在一定范围内有限的选择权,来取代一般意义上的真正的“选择权”;以仅有一定范围才可见的知识和智慧,来取代一般意义上的“所有”的知识和智慧;以在这个世界上只占一少部分的“城市繁华”,来取代一切“现代文明”;以语言、手艺、旅行等十分有限的范围,取代本应该毫无限制的“兴趣”。
有人归纳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后浪”需要花多少钱,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倍;也有人只随意取材,便能展现出在“后浪”之外艰难求生的另外一群青年的生存图景;更有人直言不讳,能选择不应当仅仅是兴趣爱好。

有时间和金钱把“高达”手办当手艺
“后浪”们的生活,可能连全部青年群体的1%都不到,却用来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全部青年。
同样的,正有一批人以极少部分青年的意见,取代全部青年本应各不相同的意见,并美其名曰“后浪”。
这是不是“新话词典”当中的一个新词呢?没有人希望把生活过成小说。
“后浪”是个伪命题
1978年,我的父亲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十分高兴。
虽然他是当年的应届生,没有过学业中断的体会,但他依然庆幸自己不是处于时代谷底的那一个。
那个年代的人,喜欢一边吃大亏,一边很高兴,他们的机会先被剥夺,再还给他们,就十分感谢还给他们机会的人。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下一代人,也就是我,就不太能理解这种心情。参加高考、上大学,本应是公平提供给每个人的选择机会。
列宁的兄长因为刺杀沙皇,被处以死刑,但列宁依然顺利考入喀山大学。
后来列宁因为参加反对沙皇的运动被学校开除,沙皇当局还是网开一面,让列宁参加毕业考试拿到了学位。
列宁是不是就因此感谢沙皇,不再追求改造俄罗斯呢?
理虽如此,实际却不是这么回事。
等到我也行将步入中年,才渐渐明白,拥有并不是那么容易,保住自己已经拥有的,更不是天经地义。
在谷底的人,仰望谁都是大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能选择的越来越少,但我依然庆幸自己曾经拥有过的。

伪命题
当我还是个青年,尚未深刻体会这个道理,长辈就会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但如今我也明白了,人做不了时代的弄潮儿,长辈还会说一代不如一代吗?
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每一代人都有爷爷,每一代人也都有孙子,爷爷不理解孙子,更不理解孙子的孙子。
孙子不一定不如爷爷,孙子的孙子,也不一定强过爷爷的爷爷。
长江后浪推前浪,让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并不是后浪,而是时代的洪流。
哪有最好的时代
1971年,麦理浩出任第25任港督。
当时,这座城市面临着大量外来流民问题,贫富差距突出。
具有福利主义左派思想的总督麦理浩上台以后着力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提出了居屋计划,力求做到居者有其屋。

麦理浩(1917年10月16日-2000年5月27日)
此外他的改革措施还涉及廉政、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
在麦理浩的治下,居屋计划取得巨大成功,经济也开始转型升级,从轻工制造业转型为电子工业和金融业。
一位著名学者评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座城市发生的变革,认为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理想国”时期。
但在两所著名大学里,深受左派甚至极左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依然对现状表示严重不满。
他们批评麦理浩的政策无法彻底解决住房问题,也较少于教育领域着力,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一些青年学生甚至提出要把资产大于10万的人全部打成“黑五类”。
青年天生就是会对现状不满的一群人。
不论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还是20世纪下半叶的南方左派青年。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工体馆演唱了《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
80、90年代,青年读着《走向未来》丛书,哼着崔健的“一无所有”;世纪之交,青年羡慕韩寒能写出《三重门》,不能理解父母在独生子女身上倾注的全部希冀。
叛逆是青年的基因,当他们不再叛逆,说明他们老了。
每一代“前浪”,面对“后浪”的叛逆,总是会抱着审视、苛责、不满的态度。
我还没听说哪个上一代人可着劲儿夸赞青年,如果这事儿发生了,可得小心点。
相应地,青年会特别希望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态度、力量,告诉世界这里少不了他们。
如果某个时代的年轻人,真的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不知道是时代出了问题,还是年轻人出了问题。
结语
不可否认,确实有那么一小撮年轻人,享受到了“最好的时代”赋予他们的选择权。
正如我认识的那位在澳洲留学生活的女孩一样。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某站的用户号称上亿,难道这亿万青年都能过着同样的生活吗?
显然不可能。
用一小撮人的想象中的生活代替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触碰到了良知的底线。
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但并不是每一代人都能做好,否则历史就不会有那么多起承转合,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倒退。
一代不如一代,一代胜过一代,这既是随机事件,又不是随机事件。
下一代人如何生活,如何看世界,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上一两代人手里,取决于上一两代人把时代搞成什么样子交给后辈。
作为“前浪”的我们,还没有死在沙滩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完)